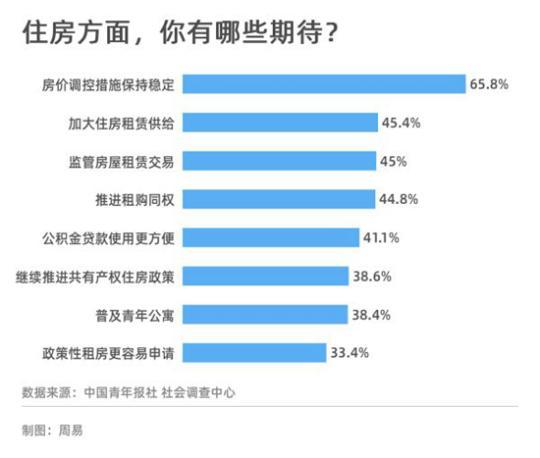乍一看几与儿童涂鸦无异的抽象画,常常看得人们一头雾水。而事实上,抽象艺术意味着更高的审美门槛。
最近,抽象艺术正成为申城海外名家名馆特展的一大焦点:抽象艺术先驱康定斯基在中国的首次大展、中国迄今最大的胡安·米罗展“女人·小鸟·星星”相继登陆,浦东美术馆与英国泰特美术馆合作的“光:泰特美术馆珍藏展”、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中心合作的常设展“万物的声音”同样汇集了一些抽象名家之作。这些重磅展览均为大众理解抽象艺术提供了绝佳的面对原作的契机。本期“艺术”,让我们聚焦抽象艺术。
——编者
20世纪的现代艺术圈宛如一座巨大的环形运动场,挤满了年轻气盛的运动员。他们迫不及待地告别曾经风行的写实主义、象征主义以及印象派,举起大旗,争相进入各自的跑道:后印象派、野兽派、表现主义、立体主义、未来主义、辐射主义、俄耳甫斯主义、至上主义、构成主义、纯粹主义、风格派……这些叱咤风云的流派多属于短跑或中、长跑赛事,唯有抽象艺术是一场跨越赛道的接力长跑,而且选手们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接过了谁的接力棒,领跑一段。康定斯基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,时下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展出的“抽象艺术先驱:康定斯基”大展便是印证。
【抽象艺术之父花落谁家】
艺术家推开抽象艺术之门为何多在中年以后?这项艺术操作实在不是仅凭直觉与想象就能完成的,需要坚定的意志才可抵达
然而回到1935年,近70岁的康定斯基却为一个问题感到不安,那就是世上首张抽象作品的作者是否属于自己。康定斯基特意写信给纽约的画廊主纽曼,说明他早年的那幅“右上角带圆圈的画,真的是世界上第一幅抽象画”。身为画家也是理论家的康定斯基太知道这个问题的“重要历史意义”了,他强调“当时没有一位艺术家创作这样的作品”。可这还真不好说。
所谓“这样的”是指最早一批去掉模拟对象物态的画作,在1911年之前,来一次史上第一幅抽象画的PK,至少还有五位画家位列其中:德国的阿道夫·赫尔策尔,荷兰的彼埃·蒙德里安,捷克的弗朗齐歇克·库普卡,法国的罗伯特·德劳内,和俄国的米凯尔·拉里昂诺夫。最早的画作来自于赫尔策尔1905年的一幅油画,以蓝色为主调、黄、红色依次减少的比例画了大小不同的三角形色块。然后到了1909年,蒙德里安的《韦斯特卡佩尔灯塔》,以大面积的蓝色和黄色的平行色点铺满画面,灯塔并无可见;库普卡的《第一步》在两个大圆环下画了11个小圆环,不知何意。1910年,拉里昂诺夫画了一些放射状的光柱,德劳内《城市之窗,第4号》的色点图案就像一个几何化的万花筒。显然,这几件或者更多的类似作品,都可以称得上是抽象画。
再看康定斯基这幅《带圆圈的画》,又有什么不同呢?起初觉得似乎是一张人的面孔,又或是某种动物,但你很快就放弃了捕捉完形,只觉得画面色彩鲜活,气氛欢愉,结果如你所愿,各种愉快的事物在其间涌动,似乎都可以从中变形出来。假设康定斯基此后见过以上这些画作,他强调的哪里是第一幅抽象画的问题,晚年的他在意的是自己作为一介先锋,在一众抽象艺术先驱中居于何等地位。
塞尚一句“要用圆柱体、球体和圆锥体来处理自然”影响甚众,“现代艺术之父”的桂冠给了他不容置喙。然而“抽象艺术之父”归谁这个问题,至今难以定论。唯一能确定的是,最初艺术家推开抽象艺术的门多在中年以后,他们画出首幅抽象画的时间,赫尔策尔52岁,康定斯基45岁,蒙德里安和库普卡年近40岁。现代艺术家里多的是像焰火般喷发的青年才俊,梵高、莫迪里阿尼、劳特雷克等都在40岁之前完成自我并谢世。但抽象艺术实在不是仅凭直觉与想象就能完成的艺术操作,它是一条兼具感性与理性的崎岖道路,既需要充沛的情感还需要清晰的逻辑,更需要坚定的意志才可以抵达,并且历尽艰辛抵达的还只是某一座小山峰,那更高更美的还不知在何处。
六位抽象艺术先驱,生年跨越了40年,最小的德劳内可以喊康定斯基为叔叔了(事实上西岸美术馆前段时间结束的与蓬皮杜中心合作的“时间的形态”常设展中,这六位艺术家的作品悉数现身)。康定斯基出道晚,1896年,30岁的他才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教职抽身去德国学艺,却又不晚,他不经意地站在了一个制高点,等到各种精神资源成熟时便加以汲取,又审时度势地使自己处于最佳的创作环境。自从1911年灵感迸发之后,康定斯基就进入了一条灵与智的上升通道。
【色彩与音乐的赋格】
抽象绘画的赛道上,标举“色彩”的各式小旗招展,而调动感官需要对节奏和韵律的掌控,这正是音乐和舞蹈的强项
在抽象艺术至今仍在继续的接力长跑中,是谁打响了发令枪?
也许是隐居在布列塔尼的高更。1888年,康定斯基还在做法律、经济学的学霸,比他年长3岁的保罗·塞律西埃已经是巴黎朱利安美术学院的班长,他去阿旺桥写生时遇到高更,被指点要简化一切,“不要尝试精准地复制大自然。艺术是抽象的过程,应该从大自然中提取”。塞律西埃听从后随手在烟盒上画下了眼前的风景,画中不见树木、流水的形态,只有一些色块的浮动,这幅画让他的几位同学一见倾心,以为是得到了艺术的福音,将之奉为《护符》,并自诩为“纳比”派。1903年,同样信服高更的摩里斯·德尼在纳比派纲领中写道:“一幅画在呈现一匹战马,一位裸体女子或者是任意的成像之前,首先是一个覆盖有按一定秩序铺好的颜色的平面。”与此同时,这些美好的色彩平面已经在博纳尔、维亚尔的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由此看来,称塞律西埃为抽象艺术的“先知”不为过。
事实上,绘画从立体主义走向抽象是一条捷径,但康定斯基在慕尼黑不在巴黎,这使他未能及时地接触到那群终日琢磨怎么把物体肢解、分割成几何切面再重组的年轻人。自从第一次被莫奈《干草堆》那种梦幻般的色彩震撼,他学会了用彩色斑点笔触和明亮的色彩作风景写生,在印象派的光影里徘徊了10年,终于感受到“非再现”绘画隐约的号令:让绘画对象“消失”吧,可怎么消失呢?康定斯基在德国小镇穆瑙的户外写生到1908年初露端倪,色彩的存在感逐渐大于事物的形状,物体轮廓倾向于几何化。
殊知康定斯基并不孤独,法国画家再一次接近色彩的奥秘。1909年,德劳内研究了化学家谢弗勒的色彩学和新印象派的作品后宣称:“色彩本身就是形式和主题”,他首次赋予了色彩在绘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,一种共识在巴黎艺术圈达成——“颜色的粒子与线条一样有可评估的抽象价值”。三年间,库普卡把女人简化成色块,德劳内把巴黎风景简化为色点,不想描绘任何物体的拉里昂诺夫弄出一束束交叉的彩色线条。到1911年,抽象绘画的赛道上,标举“色彩”的各式小旗招展。
但仅有色彩是不够的,抽象绘画如何调动感官?需要对节奏和韵律的掌控,这正是音乐和舞蹈的强项。康定斯基早就是个业余大提琴手,1911年他听了勋伯格那种音调结构无从捉摸的音乐之后,顿觉遇到知音,开始用色彩即兴创作,画出题为“印象”“即兴”“构图/作曲”的系列作品。他还写信给勋伯格,赞美其无调音乐将音乐简化,去掉主音,让每个音符都同等重要,是为了创造“新的和谐”。1912年,库普卡反复画一种叫做紫穗槐的植物,将之命名为“两种颜色的赋格曲”,诗人纪尧姆·阿波利奈尔以此为范例,请出古希腊的诗歌和音乐之神俄耳甫斯,宣告一种全新的纯粹绘画“俄耳甫斯主义”诞生,那就是用抒情色彩和自由联想造成律动感,使绘画达到音乐般的纯粹情境。同年,喜欢跳舞的富家子弟弗朗西斯·毕卡比亚画了《在春天跳舞II》,不见人形,未来主义者吉诺·塞维里尼也画了《舞者》,意在表现某种动力理论,不自觉地走入半抽象。
然而,正如毕卡比亚问阿波利奈尔的问题:“圆与三角、体积和颜色就不如桌子那样容易理解吗?”是的,彼时的评论家纷纷感到困惑。1912年,康定斯基在柏林的首次个展、毕卡比亚在巴黎的展览以及俄耳甫斯派的作品都遭到了批评,毕卡比亚的《春天》被说成是“一堆红黑色的刨花”。
此时,康定斯基出版的著作《论艺术的精神》显得相当及时。书中认为,艺术必须关心精神而非只是手工技巧,必须以触及人类灵魂的原则为唯一基础,通过色彩来达到,且色彩不只是带来愉悦的身体体验,而是能触动灵魂的“内在共鸣”,这便将色彩提升到人类精神生活的高度。但这还不够,它就像音乐那样:“色彩是琴键,眼睛是琴锤,而心灵则是钢琴的琴弦。画家则是弹琴的手指,他按动各个琴键,引发心灵的震颤。”通过这种联结,康定斯基笃定要打破绘画僵硬的线描痕迹,让抽象的形状在画布上流淌,就像音乐家谱曲那样自然。色彩也被比附为各种乐器——淡蓝色的长笛,深蓝色的大提琴,藏蓝色的巴松管,绿色的小提琴,红色的小号,紫色的木管……从而画家落笔之际,就像听一首交响乐般来观看自己的作品。不管康定斯基的这番论述当时的人们是否听得懂,抽象艺术的根基稳了。
【圆形与方形的奏鸣曲】
数学中的圆形和方形最受抽象派画家青睐,康定斯基属于圆形一派,方形主要靠马列维奇和蒙德里安两位独行侠
经过对色彩的集体开悟,抽象派画家们进一步向线条和几何形状开掘。数学中常见的直线、曲线、方形、圆形、三角形此时成了主角。三角形不太受宠,它在古典绘画的风头(隐形的)已过,最受青睐的是圆形和方形,各有阵营。
康定斯基属于圆形一派,在他之前,最早画圆的是俄耳甫斯主义者。
库普卡1909年就画了圆环,接着有《圣母院》(1911)、《牛顿色盘》(1912)这样典型的作品,此后20年他围绕一个点展开圆环,寻找线、面与空间的关系。德劳内的妻子索妮亚在家中的墙壁涂画自己调配的新色彩,不久德劳内画出了他的“圆盘”系列(1912-1913):一个圆盘里有多种颜色,相互交叠,画中像有一个旋转的螺旋桨,一些离心的曲线从一个燃烧的太阳中心辐射出来,引起五光十色的色彩颤动。
俄国构成主义者紧随其后。十月革命后,亚历山大·罗德钦科用红、黄、黑色在画面正中放上大圆形,再用色差表示其在旋转。埃尔·利西茨基画了黑色的圆,又画了白色的圆被一个红色楔子穿进到中心点,暗示当时的俄国内战中红军打败了白军,以此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。同时期康定斯基在俄国,沉浸在红色与其他颜色的争斗、曲线与直线的较量中,但弓形和半圆环线条也渐渐增多。1921年底康定斯基重新回到德国,圆已成为他的中心母题。最初的《蓝色部分》(1921)画面周边分布的一些小圆色块只占很小的比例,《小宇宙》(1922)中圆逐渐扩大,《构图8号》(1923)变得很大,《圆中有圆》(1923)的大圆已经占据整个画面正中。《几个圆形》(1926)中,从黑色空间里浮起了一些轻盈透亮的粉彩色圆形,它们相遇相交,又慢慢离去。这种浪漫与神秘在《玫瑰色重音》(1926)中,以画面偏右上方的那个粉红色圆形达到高潮。
有趣的是,方形稍晚于圆形出现,主要靠两位独行侠。俄国艺术家卡济米尔·马列维奇先声夺人。1913年,蒙德里安还在一点点地摸索着对树的简化,马列维奇在一张白纸上用直尺画上一个正方形,再用铅笔将之均匀涂黑,名为《黑方块》,两年后他把这幅画拿到彼得格勒“最后的未来主义绘画0、10”上展出,观众纷纷叹息,“我们所钟爱的一切都失去了……我们面前,除了一个白底上的黑方块以外一无所有!”马列维奇同时发表“至上主义”宣言,认为在绘画中纯粹感情或感觉至高无上,这种理论比康定斯基的“艺术的精神”决绝得多,他要做的是把绘画的表现性因素彻底排除,难怪早年会被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三次拒绝了。所幸马列维奇在35岁时顿悟,最简单的形式——方块就是不带任何感情因素的直角系统。40岁时马列维奇又推出了更加极致的《白上白》,白底上一个白方块微微向右倾斜,仿佛要弥散开来,此时不仅体积、深度消失,所谓物体、空间都变得毫无意义。五年间马列维奇似乎让方形走到了尽头,蒙德里安还怎么做呢?蒙德里安直到1917年才简化出三种颜色的方块,刚刚把色块装到大小不同的方格子里,就面临马列维奇这种否定意味的白色沉默,他却是十分坚定又乐观的投入“新造型主义”的抽象,以节奏和韵律的和谐为目标稳扎稳打,1921年他提炼出三原色加三非色、水平线加垂线的网格结构,又坚决的剔除用对角线(与好友决裂),最后成为现在最著名的格子大师。
当马列维奇的《黑方块》像一记重重的鼓点震动艺术圈时,康定斯基也在其列,对于俄罗斯民族的智慧,他既能敏锐地捕捉到,又选择性地吸收。他曾与年轻激进的拉里昂诺夫通信,了解“光滑动所造成的超时空感觉”实验所带来的四维体验。构成主义者对他不友好,但《黑色关系》(1924)可见利西茨基《Proun 5》(1920)的痕迹,《玫瑰色重音》引入了方形,《汇于点上》(1928)的三角形托起了圆形。俄国的神智学启发他领悟了“艺术的精神”,并让他的浪漫主义从冰里燃烧出火焰。
行文至此,又闻浦东美术馆正在举办“胡安·米罗:女人·小鸟·星星”展。西班牙艺术家米罗在康定斯基发表《点、线、面》的前一年以“梦幻绘画”成名于巴黎,他独创的神秘符号、稚拙线条与迷幻色彩以及看似童趣般的画作,颇受人们喜爱,成为名望仅次于毕加索的西班牙现代派大师。米罗将抽象意境与超现实的心灵体验完美融合,也可以看做是康氏理论的绝佳演绎。
因而19世纪末的先驱们开创的抽象艺术赛道是一场马拉松,直到今天,这场马拉松仍在继续,看来没有终点。(颜榴 作者为艺术史博士、柏林自由大学访问学者、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)
凡注有"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"或电头为"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"的稿件,均为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独家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;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"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",并保留"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"的电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