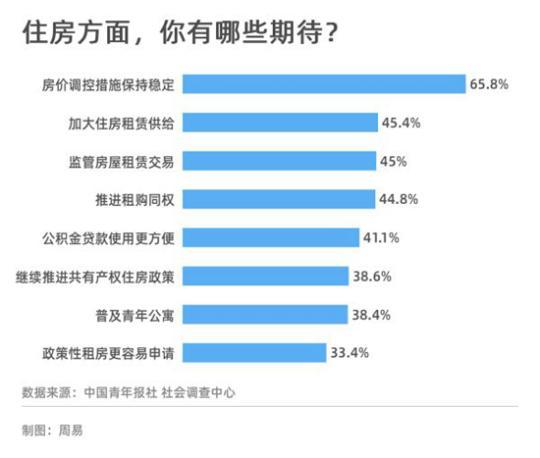艺术创作中生与熟具有辩证关系。
宋代韩驹说:“作语不可太熟,亦须令生。近人论文,一味忌生语,往往不佳。”何以用熟语创作出来的作品欠佳呢?胡仔解释说:“事浅语熟,更不思究,率尔用之,往往有误。”从文艺心理学角度看,正因为用语太熟,文人不经思考便“率尔用之”,致使创作进入了无意识的自动化状态,结果就出现了纰漏。胡仔的说法有点流于皮相之谈,其实这样炮制的作品即使没有错误,也终究是满纸套语,缺乏新意,难以摆脱平庸的宿命。
王直方在其《诗话》中说:“圆熟多失之平易。”沈德潜在《说诗晬语》中说:“过熟则滑。”表现的圆熟,读者虽然易于接受,但失之于顺滑,留下的印象必不深刻,因此接受效果难免会打折扣。表现的圆熟,还给人似曾相识的陈旧感,让人产生审美疲劳,甚至滋生排斥和逆反心理。有见识的作家,都知道处理好诗文生与熟的关系。蔡絛在《西清诗话》中记载,“王仲至召试馆中,试罢作一绝题于壁云:‘古木森森白玉堂,长年来此试文章。日斜奏罢《长杨》赋,闲拂尘埃看画墙。’荆公见之甚叹爱,为改作‘奏赋《长杨》罢’,且曰:‘诗家语如此乃健。’”把“日斜奏罢《长杨》赋”改为“日斜奏赋《长杨》罢”,王安石只调换两个字的位置,就充分凸显了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差异,在表达效果上化惯常为新鲜,化熟悉为陌生,同时也有一股内在的劲健灌注其中。魏庆之在《诗人玉屑》“语不可熟”条中说:“东坡作《聚远楼》诗,本合用‘青山绿水’对‘野草闲花’,以此太熟,故易以‘云山烟水’,此深知诗病者。”苏东坡深谙“熟”的危害,于是改弦易辙,以陌生化的方式进行应对。陌生化理论认为,“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,使形式变得困难,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,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。”苏轼的对句,打破了常规,给人一种春风拂面的新鲜感。现代作家周作人的散文将日常口语、欧化语与文言熔为一炉,日常口语简单平易,读起来很顺畅,但也容易一滑而过;欧化语、文言则让人觉得蹇涩,读起来觉得不那么顺畅,需要放慢速度,花费较长的时间,才能够透彻地理解。简单味与涩味的统一,其实也是熟与生的杂糅调和,周作人如此编码,散文便自成一家,别有风味。
对艺术世界完全陌生,当然不可能创作出作品;只有具备了基本的艺术素养,对前人艺术成果有所熟参,对艺术形式上的规则了然于心,艺术家才能进行创作。由此可见,艺术创作是基于“熟”的基础上的。但是熟了之后还须能“生”。清人王澍说:“书到熟来,自然生变”;郑板桥也说:“画到生时是熟时”,他们的表述都隐晦地蕴含有这一要求。常言亦道:熟能生巧,所谓“生巧”就是生出新变,生出妙趣的意思。需要说明的是,这种新变,须反常而合道。熟后不能生,艺术就了无新意,创作的意义将大打折扣。反常而不合道,艺术就步入了险怪一途,其接受和评价将受到影响。艺术创作从生到熟,又从熟到生,这一螺旋式上升的过程,就是艺术自我圆满、自我突破的过程。
明代诗论家谢榛说:“贵乎同不同之间,同则太熟,不同则太生”“能近而不熟,远而不生,此惟超悟者得之。”清代沈德潜认为:“唯生熟相济,于生中求熟,熟处带生,方不落寻常蹊径。”以此观之,前人对艺术生与熟的搭配,已有明确的意识,只是没有具体量化而已。在当今这个崇尚科学、一切都趋于量化的时代,艺术作品中生与熟的比例是多少才好呢?有研究表明,70%的熟悉,30%的陌生,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。70%的熟悉,就是说要有这个比例符合读者的成见,读者才乐于接受;30%的陌生,则表明作者的创新须达到这个比例,才能给人以新鲜的感受。需要指出的是,即使深谙“三七开”这个公式,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文章要写得好,还有很远的路要走。
古人今人如流水,几乎每个文人都感叹余生也晚,好文章被前人写尽了,好语言都被前人说完了。丰厚的文学传统对每个作家都构成了压抑,因此影响的焦虑在所难免。如何进行创新,前人进行过艰苦的探索。梅尧臣主张“以故为新,以俗为雅”;黄庭坚倡导“点铁成金”和“夺胎换骨”;阮阅则说:“熟语贵用之使新,语如己出,无斧凿痕,斯不受古人束缚。”说的都是要以旧为新,把熟悉的内容用出新意,使之既似曾相识,又截然不同。只有这样,才真正做到了“后进追取而非晚,前修久用而未先”。
既要避生,又要避熟;既要熟,又须熟而能生,艺术创作中生与熟的问题,简单又复杂,关涉技与道,能不高度重视吗?(朱美禄贵州财经大学教授)
凡注有"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"或电头为"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"的稿件,均为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独家版权所有,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;授权转载必须注明来源为"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",并保留"实况网-重新发现生活"的电头。